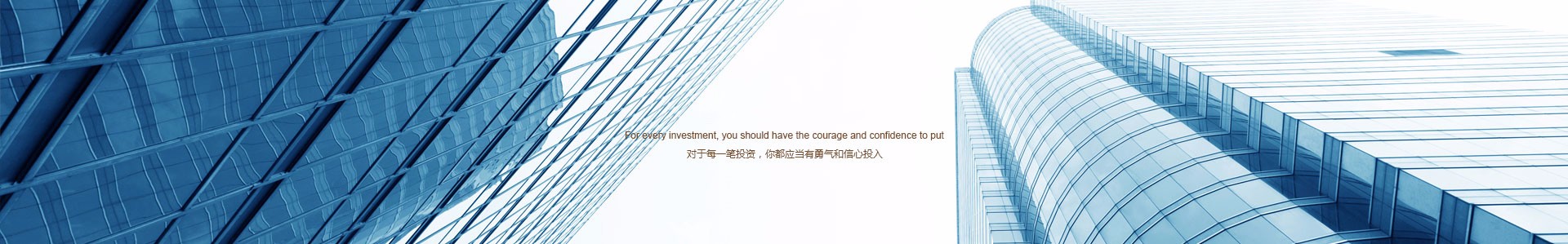《金融博览·财富》|以制星空体育- 星空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度生态建设赋能特殊需要信托高质量发展
2025-09-30星空体育,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APP下载/星空体育官方网站(xk-sports)亚洲卓越在线公司[永久网址:363050.com]星空体育,星空集团,星空体育官网,星空体育app,星空体育网页版,星空捕鱼,星空体育app下载,星空体育官网,星空体育下载,星空电竞,世界杯,足球,星空体育入口,星空体育网址,星空体育全站,星空体育注册网址,星空体育注册链接,星空APP下载,以安全稳定的服务和打造星空体育app而闻名海内外。

当前,契合特需人群安养实际需求的特殊需要信托实践,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架构设计。
如何将特殊需要信托设计纳入法律制度框架之中,构建更加良好的制度生态,以更好地发展真正服务于特需人群的特殊需要信托,值得深入探讨。
特需人群主要包括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年人和生活无法自理的残障人士等。他们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面临安养困境。他们之中,有的人缺乏正常的识别和判断能力;有的人缺乏金融或法律的专业知识,无法亲自处理安养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对于履职不当的监护人或受托人提出合理的权利诉求等;甚至有的人无力应付亲属的欺诈以及对其财产的觊觎。
委托人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的目的在于为特需人群提供长期照料,以确保其维持委托人在世时的生活品质和人格尊严。为实现这样的目的,特殊需要信托应发挥多方面的制度功能。
首先,发挥信托隔离财产功能,确保委托人留给特需人群的财产用于其生活和消费。委托人的财产包括各类有价值的财产,如不动产、股权、无形财产和资金等。上述财产均可依法转移至信托名下,成为独立的信托财产,由受托人依照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进行管理与处分。同时,受益人对于信托财产的受益权应作保护安排,以排除不合理的外来干预和侵占。
其次,设计一个角色就如何照护特需人群做出决定,从而保障特需人群的生活品质。这个角色可以是监护人,也可以是受托人,他们可以成为信托事务的指令权人。通常而言,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并不擅长于此,委托人信任且能提供专业意见的人士适合担任此角色。若特需人群生存期间跨度大,或因情事变迁,还需要提供顺位人选。
最后,妥善设计特殊需要信托中受托人、监察人、指令权人等的权利与义务。特殊需要信托不同于普通的投资信托,往往存续较长时间。各方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设计,直接影响信托架构的稳定性,关涉特需人群的权益保障。遵循权责一致原则,既要避免权利过大而责任畸轻,也要防止权利微小而责任畸重。
讨论委托人的范围,主要是要明晰哪些主体可以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特需人群自身及其父母子女可以作为委托人设立自益或他益信托。在现有实践中,还出现过以特需人群住所地的居委会担任委托人,将特需人群的财产交付信托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的案例。对此,市场上也有不同的声音。
支持者认为,由于特需人群已无其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而我国《信托法》规定委托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迫于信托公司的要求,只能由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故而设计了该信托架构。
反对者则认为,居委会即便出于现实考虑,也不是适格的信托委托人。委托人需要用自己的财产为受益人设立信托,而该案例中设立信托的财产是受益人自有财产,不符合信托法理。
笔者认为,设立信托的财产应为委托人的自有财产,这是各国信托法的惯例。以自有财产为他人设立他益信托,法律上应将其认定为对他人的财产赠与。前述案例中,居委会应以监护人身份为特需人群设立自益信托,而非以自己为委托人设立他益信托。
委托人设立信托后,通常会退出信托关系,这是英美传统信托法的惯例。为凸显委托人的意愿,各国信托法往往允许委托人保留一定权力,甚至会设立可撤销信托。特别是离岸法域,为吸引高净值人士前往设立家族信托,往往允许委托人保留干预信托的权力。大陆法系国家因无衡平法传统,在引入信托法时已有较发达的民商事法律,特别是合同法,引入信托法多以促进金融理财制度为目的,因此,当委托人以合同方式设立信托时,作为合同当事人之一的委托人,即保留了诸多干预信托运行的权力。
我国的信托法律亦不例外。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委托人拥有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式、解任受托人、撤销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行为、变更受益人等权力。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委托人过度控制信托可能会被认为设立信托系虚假的意思表示,甚至信托事实上并未真正设立,从而无法产生信托财产隔离的法律效果。
委托人保留权力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当委托人去世后,其所保留的权力由继承人继承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信托的存续。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如特殊需要信托被委托人的继承人撤销,可能令其陷入困境。因此,即便委托人希望在生前保留对特殊需要信托的实际控制,也要考虑到其对信托权力继承后可能发生的影响。委托人保留权力应当与信托设立形成平衡,避免因委托人过度控制信托而影响信托效果。
对此,笔者建议,信托法可针对特殊需要信托明确委托人不得设立可撤销信托,同时在继承制度上明确特殊需要信托委托人权力继承的限制,委托人的继承人行使继承权不得损害特殊需要信托受益人的权益。
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承担的注意义务较之其他信托的受托人,究竟应当更重还是更轻,涉及其义务标准问题。当前,信托受托人皆为信托公司,其对于如何妥善处理特需人群的照护与安养问题,其实并不专业。如果对受托人要求太严、责任太重,可能会影响特殊需要信托的推广。
在比较法上,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往往承担消极义务,通常是作为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以确保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收益分离,从而维护信托的本质,实现财产隔离的功能。受益人的照顾则交由监护人或保护人以指令权人身份,作出决策。监护人或保护人因更了解特需人群的照护需求,适合为其选择更为适当的康复及治疗方案。
在我国目前的特殊需要信托架构下,受托人通常负责财产管理,并接受监护人或其他指令权人指示,为了受益人利益而处分信托财产。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目的审核指令,但如果要求他们从专业角度判断指令是否合理,现实中很难做到。这类监督工作,还是由专门的监察人来负责更合适。
因此,笔者建议,信托法上应为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确立合理的受托义务,以其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归责与否的判断标准。
当然,确立合理的受托义务标准并不意味着受托人可以任意签署免责条款。由于实务中信托文件多由受托人拟订,受托人往往会将各类免责条款装入信托文件,以尽量减轻自身的受托责任。综观各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免责均设置了限度,即便是仅仅充当名义所有人的消极受托人,亦有最低限度的受托义务。在信托法确立特殊需要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标准的同时,也应明确其最低限度的受托义务,以保障特殊需要信托受益人的权益。
监护人通常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监护制度选任,在设立特殊需要信托时,被监护人作为信托的受益人,其权益受到信托制度的保护,监护人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监护人可以作为特殊需要信托的指令权人,介入信托关系,以发挥其对被监护人的人身照顾职责。除此之外,委托人还可以设置监护人之外的其他指令权人。指令权人就信托财产如何分配、运用于受益人的医疗康复、生活娱乐等事项对受托人进行指令。这也是实务中特殊需要信托通常采用的制度设计。
此种设计存在的问题是,指令权人是否应承担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及责任。各国信托法对此并无统一规定。英美信托法大体上遵循权责相符原则,通常要求指令权人承担一定的受托义务及责任。离岸法域则多明文规定,在委托人将权力保留予指令权人时,受托人得以相应豁免其责任,而指令权人应否承担受托义务则有不同立法。有的规定,指令权人并不会因此成为受托人,如泽西岛信托法、BVI及巴哈马等;有的则规定,信托条款应对此作出相反规定,如根西岛;也有的规定,除非信托文件明确豁免,否则指令权人原则上应负受托义务,如百慕大。
是否将指令权人纳入受托人范畴,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指令权人应负信义义务,但并非受托人,原因在于其与委托人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信托合同关系,且信托财产并不归属于指令权人,而是在受托人名下。由于指令权人系实质上对特殊需要信托事务作出决策之人,其与信托公司均作为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受托人,且有明确分工,因此将其与信托公司认定为共同受托人也无不可。
实务中的指令权人,还可能以信托保护人、信托顾问、信托指示人等名义出现。这些接受委托人指示,能够实质影响信托事务管理及信托财产投资与处分的主体,均应与信托公司作为共同受托人,承担信托受托人的义务与责任。当然,由于存在明确的分工,共同受托人并不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对其各自负责的事务承担责任。
对此,笔者建议,我国《信托法》亦应修改相应条款,增设共同受托的分别责任规定。
为避免信托财产成为债权人追讨偿债的对象,从而危及特殊需要信托受益人的权益,应增设保护信托、禁止挥霍信托与裁量信托等信托类型,以保护信托财产与受益人的受益权。
保护信托的显著特征在于“没收条款”,即受益人发生一定事件时,受益权即被没收,自动消灭,信托转为以该受益人配偶及子女为潜在受益对象的裁量信托。
禁止挥霍信托的最大特征在于“禁止转让条款”,即受益人不得基于自愿或被动转让受益权。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往往处于自身无法理财的弱势状况,通过此类信托可以避免财产损失殆尽或被骗等意外发生,保障其生活。
裁量信托则指受托人(或委托人指定之人)就信托利益的分配享有广泛甚至绝对的裁量权,可以完全不予分配,或只对特定对象分配,且具体分配金额也由受托人决定。当特殊需要信托受益人的受益权成为受益人债权人偿债追讨的对象时,增设前述条款可以有效保护受益权及信托财产。此类债权限于合同之债,而不包括侵权之债。因信托财产或受益人的行为侵犯他人而应承担侵权责任时,应允许债权人追索信托财产甚至执行受益权。理由是,侵权之债的债权人系非自愿发生债的关系,无法预见信托财产的特殊性,因此不应受到信托财产保护制度的限制。
委托人与其丈夫已离婚多年,独自抚养心智障碍子女一名,拟将其前夫排除在子女照顾人之外,由其指定的亲属作为监护人,待其百年之后作为为孩子设立的特殊需要信托的指令权人,决定信托财产运用于其子女的事项。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负责管理其名下所有财产,并按照指令权人的指示拨付财产给受益人或照护机构。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父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子女的当然法定监护人。委托人身故之后,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通过遗嘱指定其子女的监护人,但因现行法律并未明确,遗嘱指定监护人与法定监护人发生冲突时,应由谁担任监护人的问题。一旦涉及诉讼,法院会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
如果委托人的前夫担任了监护人,就可以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由于委托人的财产已交付信托公司,但其子女享有的受益权也属于被监护人的财产,基于受益权分配得到的信托财产收益,都将处于监护人管理控制之下。由此,可能导致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偏离委托人设计的初衷。
化解这一困境,需要《民法典》就“遗嘱监护人与法定监护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如何解决”作出明确规定,为当事人作出相应决策提供参考。
某信托推出普惠型“特殊委托人+养老直付+双监察人”特殊需要信托,由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设立信托,被监护人为委托人,且为第一顺序受益人,信托目的是提供被监护人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生活所需,监护人作为自然人监察人,律师事务所作为机构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结构,确保受托人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
根据公开报道,此信托架构设置了临时信托利益分配机制,以应对委托人医疗费用等意外支出,同时设置了相机决策救助机制,即受托人有权视委托人情况进行信托利益分配,最大限度维护其老年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
本案信托架构中,临时信托利益分配机制实为特殊需要信托实务中指令权人根据受益人的实际情况决定信托事务的设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由谁担任该指令权人,其是否承担受托人的义务及责任。相机决策救助机制,包含有裁量信托的元素。然而,针对此类特需人群,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并不专业,仍需要依赖专业机构提出建议,并由指令权人发出指令,方可妥善作出决策。